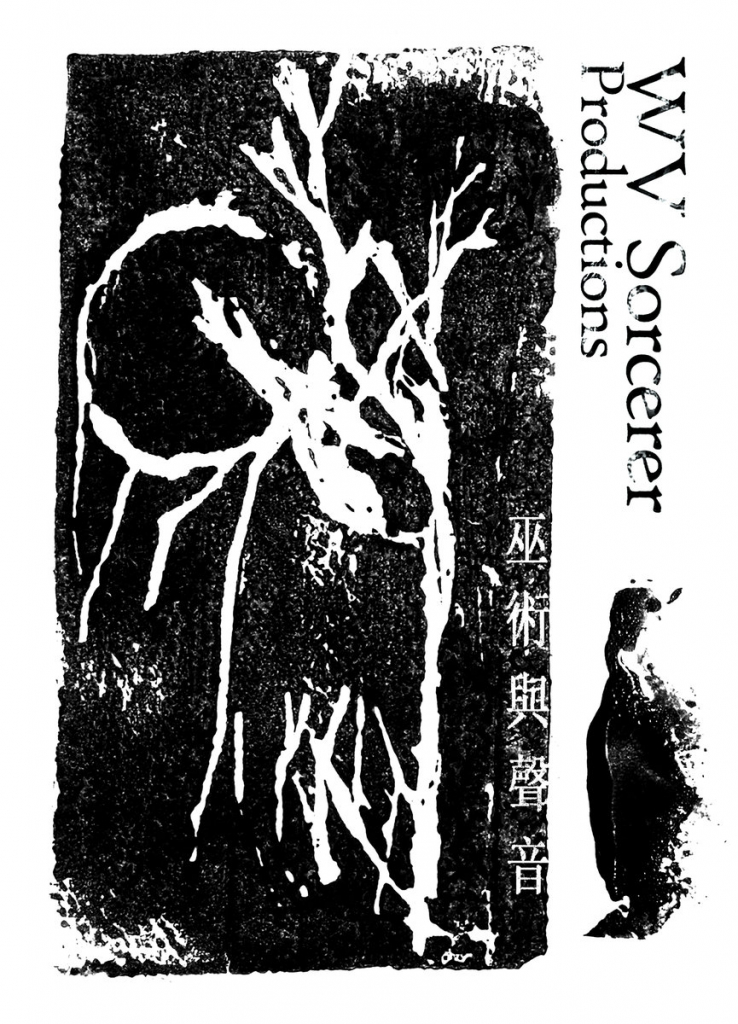作者罗亭对于当下东方迷幻、噪音类音乐的现状有自己的观察和见解。在他眼中,北京、东京、南京、台北的四家厂牌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又同时共同构成了有机的迷噪社群网络;在这种环境下,采取西方体裁的东方迷噪音乐虽然发展健康,但因“先天劣势”,似乎仍背负着无法突围西方文化霸权的宿命。 对于罗亭的观察、切入角度和阐述的一些事实,编者是认同并深感兴趣的;但就个别悲观的论断,又与他持不同观点。如果你对于流行/当代音乐在中国乃至其他“东方”国家的现状与趋势、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有话想说,请务必留言让我们知道——因为这篇文章的初心即是引起讨论,在交流中探明方向。
 “东方”是什么?正如萨义德发现的,“东方”不是孤立存在的,东方是西方想象的产物,是作为主体的西方眼中的他者。这倒应了 Temples 的那首歌,《( I Want to Be Your )Mirror》——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以人为镜,每一种文明都是其他文明眼中的他者;凝视他人,看到的却是自己。当时间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普遍有着被西方殖民经历的东亚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但是在文化上依然面临着西方无可争议的霸权时,东亚地区的人们是怎么做的?我经常听到人们评价一个日本乐队时说“不看简介还以为是欧美的”,言下之意就是:这支乐队(至少在音乐上)完全放弃了自己所在文化的特征,完全接受了西方市场的标准并尽力向其靠拢。我也常听到人们嘲讽某些唱英文的中国乐队,“人声一出来就知道是大陆的”,这就是说,这支乐队在向西方标准靠拢的方面做得不够好,没有完全摆脱本土的印记。(这方面的例子可以类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掀起的汉字拉丁化运动——那时的人们更为激进,想要一步步简化汉字并最终以拉丁字母彻底取代象形文字。)
“东方”是什么?正如萨义德发现的,“东方”不是孤立存在的,东方是西方想象的产物,是作为主体的西方眼中的他者。这倒应了 Temples 的那首歌,《( I Want to Be Your )Mirror》——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以人为镜,每一种文明都是其他文明眼中的他者;凝视他人,看到的却是自己。当时间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普遍有着被西方殖民经历的东亚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但是在文化上依然面临着西方无可争议的霸权时,东亚地区的人们是怎么做的?我经常听到人们评价一个日本乐队时说“不看简介还以为是欧美的”,言下之意就是:这支乐队(至少在音乐上)完全放弃了自己所在文化的特征,完全接受了西方市场的标准并尽力向其靠拢。我也常听到人们嘲讽某些唱英文的中国乐队,“人声一出来就知道是大陆的”,这就是说,这支乐队在向西方标准靠拢的方面做得不够好,没有完全摆脱本土的印记。(这方面的例子可以类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掀起的汉字拉丁化运动——那时的人们更为激进,想要一步步简化汉字并最终以拉丁字母彻底取代象形文字。)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审视当下的影视界。假如日剧、韩剧、甚至未来哪一天国产剧大量出口欧美,我们就能说这是东亚文化的胜利吗?显然不能。因为不论日剧韩剧还是国产剧,从形式、题材到制作工艺,无一不是脱胎于欧美剧;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欧美剧的复制品,是西方人假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之手生产出来的而已。它们若在欧美取得成功,恰恰说明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对西方人建立的这一套体系所匍匐之彻底,而它们越是成功,西方也就越是成功。为彰显本土文化,还有些人做了怎样的尝试?我们以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张艺谋的《影》为例。在《影》中有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八卦图、阴阳、竹林、水墨风、琴瑟和鸣、冷兵器;所有这些可谓将中国传统美学张扬到了极致。那么我们可以说,《影》是在凸显东方特性,以此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吗?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事实上,别说一部《影》,如今任何凸显本土文化,或明或暗地“反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尝试,不论是在电影上还是音乐上,不仅没能撼动西方对东方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反而使得这一结构更加牢固。从《红高粱》到《英雄》,从柏林金熊奖到戛纳银狮奖,张艺谋的的确确展现了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中国。但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刻意满足西方人想象的中国:张艺谋电影或者类张艺谋电影里的所有这些符号——汉字、辫子、李小龙、水墨画、阴阳八卦、毛泽东、义乌小商品市场、淘宝——构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这是一个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参照物的中国,而“西方”在这里是“文明与现代”的同义词。在音乐领域,这种符号化最极端的体现之一便是各种“二次元古风歌曲”和各种“国风金属”。巧的是,“古风”和“国风”本身就是横跨音乐、电影乃至文学、服饰等多个领域的符号,任何想要用这些符号去构建“中国的独特性”的尝试不仅不可能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相反会使得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这一形象日益牢固;西方人需要这样的一个他者来明确边界,树立自信。
当摇滚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大陆并日渐兴盛时,几乎所有的乐队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问题:从乐器(要不要使用“民族乐器”或者说“东方乐器”)到语言(该用中文还是英文)再到题材(该表现人类共通的还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具体到迷幻音乐,情况更为复杂。尽管效果器可以给人带来迷幻的体验,然而,在西方人看来,“东方乐器”似乎天然就是迷幻的、异域的、玄之又玄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George Harrison曾多次前往印度师从Ravi Shankar 学习西塔琴并写出了《Norwegian Wood》等被认为很“迷幻”的歌。也正是从那时起,为了制造出迷幻的感觉,欧美不少乐队都开始使用西塔琴,而一些亚洲乐队也开始使用西塔琴。然而问题在于:印度人是否觉得西塔琴很迷幻乃至富于“异域感”?对他们来说,西塔琴本来只不过是一种传统乐器,正如古筝之于中国人,三味线之于日本人,早已习以为常,并无特别之处。如果印度人觉得西塔琴很迷幻或者中国人觉得古筝富于异域感,那他们已经不是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而是正通过西方的视角看待西塔琴或古筝。他们在音乐中加入西塔琴或古筝以制造迷幻或异域效果,并不表明他们在张扬本土文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这表明他们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彻底服从。
如果顺从和反抗其实是同样的结果,此时就应该问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个不朽的问题:“怎么办”,有第三条路可走吗?而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没有明确答案。但是,多了解、多观察、多思考总是没错的。
为了暂时走出死结,寻找一些积极的意义,我将在下文简述四个厂牌,并以它们为主要线索来观察新世纪东方迷噪音乐的脉络。这四个厂牌分别是:北京的“Space Fruity Records”,南京/法国的“WV Sorcerer Productions”,台北的“ Lonely God Records”以及东京/阿姆斯特丹的“Gurguru Brain”。我将它们归为一类集中提出并不仅仅因为音乐、文化和地理上的接近,还因为他们之间在线上线下都有着切切实实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社群”。萨克斯乐手王子衡首张正式专辑《万火归一》于7月由WV Sorcerer Productions发行,当天则在 fRUITYSPACE做了首发演出;杭州迷幻乐队“Dolphy Kick Bebop”在Space Fruity Records发行一张磁带后,又将在 WV SorcererProductions发行一张现场专辑黑胶,还在杭州给 Guruguru Brain的看家乐队“幾何学模樣 Kikagaku Moyo”做过演出嘉宾;台北迷幻民谣乐团“落差草原WWWW”刚在9月发表新专辑《盘》——其CD版本由Lonely God Records出版,黑胶版本则由Guruguru Brain发行,而你在fRUITYSPACE也可以找到他们以前的专辑《泥土》的磁带;台北嗡鸣氛围乐队“破地狱Scattered Purgatory”长期在Lonely God Records和Guruguru Brain发行专辑,而他们今年也将被WV SorcererProductions 带来大陆,和王子衡、若潭(WV Sorcerer Productions主理人)共同巡演,而上海站的嘉宾将会是Dolphy Kick Bebop……
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厂牌的意义:与其说发行、演出等现实中的意义,厂牌更重要的意义是精神上的——它是某种价值的体现,它把有着相近品味和爱好的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或隐或现的社群;而定位相近的厂牌通过交流,又得以形成一个更大的社群。这样的社群能够孵化新人(不论是乐迷、乐手还是演出组织者),是整个音乐场景的生命力所在。
虽然主理人翟瑞欣并没有将Space Fruity Records定位为一个迷幻厂牌,但不论从logo 设计还是出品来看,迷幻显然是Space Fruity Records的基调。从最早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四头条的 fRUITYSHOP黑胶唱片店,再到美术馆东街的地下室演出场地fRUITYSPACE;2017年,Space Fruity Records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休闲、复古”是整个fruity系的精髓。在演出之外,fRUITYSPACE还会举办展览、售卖唱片、组织沙龙。在 D22 和 XP 相继关门之后,它成了 “后黄金时代”人们最后的慰藉——“世界在下沉,幸好我们还有fRUITYSPACE。”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这四个厂牌中最为特殊的;它不仅属于当下,更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美好的追忆。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Space Fruity Records 是一个有着“成熟”气质的厂牌。这不仅是因为主理人随性自然、出品休闲复古,还因为旗下大多数乐队的乐手确实早已青春不再。“Boiled Hippo”于2015年成立于北京,是Space Fruity Records最早敲定出版计划的乐队;“The Molds”则是一支在北京地下蔓延十余年的传奇乐队。两支乐队在去年九月同时发行了各自的首张七寸黑胶:Boiled Hippo的EP《谜/河》收录了乐队从传统迷幻摇滚转入新迷幻过渡阶段,三名乐手录制的两段迷幻即兴录音;The Molds的EP《4 Live Tracks at Obiwan 2010》,则是乐队多年前的一次现场录音。在 EP 发行之后,The Molds 做了一次五城小巡。在新鼓手加入变更为四人阵容后,乐队将于今年十月发行首张正式专辑《Born Astride the Grave》并进行大范围的全国巡演。在今年六月,Space Fruity Records还发行了两支江浙乐队各自的首盘磁带:杭州迷幻乐队Dolphy Kick Bebop的《Smoke a Haiku Cigarette》和义乌自由即兴乐队鸭听天的《义乌情》。同样活跃在“水果店”地下室的还有由杨帆和The Molds的刘舸组的、此前与The Molds一同巡演的TOW;由Boiled Hippo的阿炳和离开吹万后的刘心宇与李子超组成的“冲浪味”Sleeping Dogs;由李子超、刘舸和翟瑞欣组成的、擅长复古粗糙流行乐的“Mole Eyes”。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在Space Fruity Records发专辑却与地下室气质相投的乐队:常年在大陆、台湾和美国“流窜”的“工工工”以及与其如影随形的Simon Frank。两者及其前身“憬观:像同叠”和 “Hot & Cold”总能让人想起那个逝去的时代。
如果说Space Fruity Records所出品的迷幻之声富于浓浓的人情味,WV Sorcerer Productions 则在噪音和实验方面要激进彻底得多。厂牌主理人沈若潭生于南京,旅居法国。或许受益于此,其合作的乐队和厂牌也广泛得多。不仅组织台湾、大陆和欧洲巡演,WV还出品磁带、CD和黑胶。葬尸湖《弈秋》(磁带)的黑金属;王子衡《活火山》(CD)和首张正式专辑《万火归一》 (黑胶)以及老丹《思维扭曲的行动体》(磁带)的萨克斯自由即兴;李剑鸿《1969》(磁带)的吉他迷幻噪音;破地狱成员卢家齐《圆》(磁带)的合成器嗡鸣;IZ《Kelengke影子》的哈萨克实验工业噪音;“Q’uq’umatz”《Tepeu》(磁带)的印第安原住民Kraut……WV Sorcerer Productions的出品品类繁杂又有着统一的黑暗美学。更为可贵的是,若潭一向秉承着 DIY 精神,几乎所有出品的设计都由自己完成;Q’uq’umatz的磁带由特殊皮绳包装并随机附送羽毛、《万火归一》大写意的封套设计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去年若潭和王子衡、丁晨晨进行了台湾巡演;今年6月,无家、李剑鸿、王子衡及梅志勇进行了“东方噪音集结欧洲巡回”;今年11月,若潭、王子衡和破地狱 将进行大陆巡演。虽仅有一人,WV Sorcerer Productions却极为活跃,沟通起了台湾、大陆与欧洲的实验噪音音乐社群。
或许是由于地理,或许是由于人文,Lonely God Records的出品不论是音乐还是设计都充满了灵性,前卫实验与台湾山水自然融为一体。Lonely God Records以“Forests”的杜泽威(Jon Du)为首,最早是一个举办演出的组织,在自然而然地聚集了一批有着相同趣味的人后,继而做起发行。实验民谣乐团“落差草原WWWW”、嗡鸣氛围乐队“破地狱Scattered Purgatory”、合成器工业乐队“Forests”、合成器复古三人组“Eaow”、fRUITYSPACE的常客 Simon Frank等都在厂牌发行过自己的唱片。而在这些音乐人中,有不少人都与Guruguru Brain或WV有过各方面的合作。作为厂牌,Lonely God Records不仅仅聚集乐队,更为王钧、王君宏等视觉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组织”。这也使得它在专辑设计与现场演出呈现方面都十分重视视觉效果。以落差草原WWWW的logo为例,”它代表着一只飞翔的鸟,也是台湾岛屿、海洋、大地、日、月”,视觉与声音可以相互转换,都是特定美学的体现。在音、画以外,文字同样承载着厂牌一以贯之的精神——在创作《泥土》(落差草原WWWW以五人编制创作的第一张正式专辑)时,五位乐手先将自己对大自然的想象写成十二首诗,带着诗到山上、海边进行采集录音和即兴,最终回到台北后再对素材进行整合编辑;这或许足以解释为何这张专辑是如此的富有诗意。
Guruguru Brain 是从2014年的一张合辑《Guruguru Brain Wash》开始的。这张合辑收录了包括厂牌主理人Go Kurosawa任鼓手的幾何学模樣在内的21支乐队的21首歌。尽管在合集发表后,其余20支乐队里除 Dhidalah(2017年,《No Water》,10寸黑胶)外没有乐队再在 Guruguru Brain发过专辑,但“Brain Wash”依旧有着重大的意义——发行合辑是一个厂牌在成立之初让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方式:它能明确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幾何学模樣大概是最有资格回答前文所述”怎么办”这一问题的乐队;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一支使用了西塔琴的日本迷幻乐队,也不仅因为他们在欧美大获成功并已移居荷兰,更因为他们不但需要被动回答更需要主动面对这一问题。正如 Go Kurosawa 所言,他在一次次的欧洲和美国巡演之后,意识到欧美听众对当代亚洲音乐的忽视,既感到沮丧,又感到振奋,从而创立了这一厂牌以推广当代亚洲音乐。而Guruguru Brain挑选乐队的标准,根据Go 说,大致是:他在听一张专辑时,能听出乐队来自哪里以及他们所受的西方音乐的影响;而他对厂牌下诸如Minami Deutsch(《Minami Deutsch》,2015,磁带和黑胶;《With Dim Light》,2018,CD和黑胶)和Sundays & Cybele(《Gypsy House》,2015,黑胶;《On the Grass》,2018,黑胶)这样把两者融合起来的乐队极为推崇。
然而,做到”东西结合,不偏不倚”真的会这么简单,真的可能吗?当我问及他对欧美乐队使用西塔琴怎么看时,Go只是简略地回答”使用东方乐器是扩展声音和实验可能性的自然结果”。自The Beatles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使用西塔琴到现在,西塔琴仍然没有并且未来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像吉他一样的常规乐器——它仍然只是一种点缀,仍然代表着西方人对东方的异域想象。在Minami Deutsch的音乐里,我们听到的是简单、循环的节奏,而这完完全全源自于上世纪德国的 krautrock,唯一能让人想起这是一支日本乐队的大概也就只有主唱用日语这一点。在厂牌其他乐队如“Ramayana Soul”(《Sabdatanmantra》,2016,黑胶)或破地狱(《稗海遺考》,2014,磁带;《God of Silver Grass》,2016,磁带;《山险峻》,2017,黑胶)的音乐里,我们的确可以听到“东方”的声音——不仅仅在语言方面——有的属于印度尼西亚,有的属于台湾,这些元素显得幽玄、神秘、晦涩、古老。然而,这就是真正的东方吗?东方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为什么一首简简单单地歌颂男欢女爱的吉他流行歌不会让人想到东方,一首浑重幽微的合成器嗡鸣却会让人产生”东方感”?原因就在于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而在西方强势话语支配下,东方人已经习惯了用西方人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越是凸显自我特性,越是表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服从,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宿命。
这四个厂牌当然不是全部。事实上,”新世纪东方迷噪音乐”的内涵要丰富得多,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在北京,朱文博、颜峻、Maybe Noise众人虽然背景各异,但依然在 fRUITYSPACE 和美术馆组织着各种各样的实验音乐演出;在上海,有着像“Mirrors解离的真实” 和“水门汀”这样日益活跃的迷幻乐队,”三角迷幻祭”等专著迷幻音乐的系列演出;在金华,有着Dolphy Kick Bebop和鸭听天的精神故乡——义乌隔壁酒吧,而他们与上述厂牌与乐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交流,也正是这种交流促进了整个社群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总是好的。
文:罗亭
编辑:Ivan Hrozny